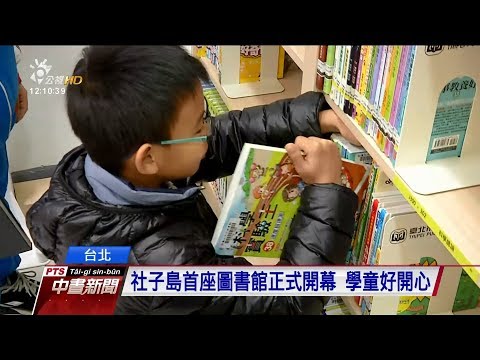想再聽你說故事——懷念作家陳柔縉(1964-2021)【觀點】

(※ 文:蔡蕙頻,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)
講到臺灣史通俗寫作,我想沒有人不知道陳柔縉。
臺灣史的通俗寫作,這幾年可以說是爆炸性的發展了,不過這個大爆炸的格局,幾乎可以說是在2000年前後由陳柔縉開啟的。90年代她寫了《私房政治——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秘聞》、《總統是我家親戚》,接著而來的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、《榮町少年走天下》寫活了張超英和羅福全,而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、《囍事臺灣》,又為臺灣史通俗寫作開了另一扇窗……。
她的著作太多,每一本都開創了一個新的格局或寫作方向,許多讀者的書櫃上都有一個「陳柔縉專區」來收藏她的書;她的文字實在太迷人了,她好像在字裡行間藏了什麼迷幻藥,人們一旦開始讀,就會忍不住一直讀到最後,一本接著一本……。
陳柔縉寫的歷史文章太好看了,所有喜歡文史的讀者,人人都在等著她的作品,她出書前後的那段時間,大家討論的都是「聽說陳柔縉要出新書了耶!」「陳柔縉的書,你看了嗎?」每當朋友問我要推薦哪一本書作為臺灣史入門讀物,我通常說:「只要是陳柔縉寫的,哪一本都可以!」我想,在臺灣史通俗寫作的領域,應該找不到第二個陳柔縉了。
採訪政壇要角,也書寫平凡小民
就因為她寫得歷史太好太精彩,以致於有些人誤以為她是歷史科班訓練出身,我記得第一次和老師聊起這件事,她揚起嘴角,瀟灑地說「我不是念歷史的」,接著解釋,其實自己念的是法律系。以歷史寫作大放異彩的她,應該很習慣眾人的誤會了吧?
她能夠把歷史人物寫得活靈活現,應該與她畢業後成為記者,因為工作的關係而採訪許多人物有關。她採訪政壇要角,也採訪平凡小市民,大量的寫作練就了她描寫人物的細緻筆法,她寫的每一個人都有豐富的靈魂。我常覺得她就像一根細而尖銳的針,穿梭在人與人之間,並在不知不覺之間把他們牽連起來,而大量閱讀,以及追根究柢地求證,讓她跨越學科,駕馭歷史寫作。
尋找與閱讀大量的史料其實非常消耗心神,陳柔縉能夠在浩瀚的史料字句中尋找、爬梳、消化,在反芻成動人的篇章,我相信對她來說並不輕鬆。
圖書館裡的陳柔縉
我是一個圖書館員,在我的印象裡,短髮的陳柔縉經常穿著白襯衫來到圖書館,質樸素雅,認識她的人應該都同意這樣的打扮非常適合她的個性。陳柔縉走路很快,動作俐落,放下行李之後馬上就遞上調閱申請單,彷彿急急地趕赴與情人相會。
她翻找資料或轉微卷膠片的時候非常投入,閱讀機的燈一亮,她便墜入歷史之中,心無旁鶩。她的粉絲太多了,其他的讀者若認出她,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,或想上前攀談幾句,但看見她專心的神情,總不忍心打斷她,只好在一旁等待,等著是否能碰到她關上閱讀燈,從史料中回到人間的時刻。
我也深刻感受到陳柔縉對身旁的人那份尊重與謙謙有禮。對館員來說,某種程度上,讀者就是「消費者」,有的人高高在上,從不言謝,有的人面無表情,公事公辦,但陳柔縉卻讓我們印象深刻,她明明是接受服務的人,又是個知名的大作家,卻總是客氣到像是服務他人的角色。偶爾一段時間沒來圖書館,再來的時候便會和館員低聲閒聊兩句,更新近況,就像是和一個久違的朋友話家常。
圖書館是寧靜場所,不宜大聲交談,她也從不打擾任何人,不刻意與人打招呼,因此我們偶爾會在書架的兩端「偶遇」,隔著書籍的間隙彼此點頭,相視而笑來代替問候,有時候她則是從書架之間探出半個身體來,向經過的我招招手,臉上依舊是充滿活力的溫暖笑容。
有一次,她調閱了許多微卷膠片,待資料備齊,她開心地抱著它們離開服務櫃台,準備去「大快朵頤」了。不久之後,她又將它們抱回來,滿臉歉意地說,剛剛接到電話,家裡臨時有一點事情,得趕快回去一趟,「抱歉麻煩你們跑去調閱,還沒看就還回來,又要請你們再跑一趟,放回去了!」陳老師,替讀者調閱資料本來就是館員的工作啊!這麼可愛的讀者,館員們都在心裡偷偷地替她留了一個位子,無論她任何時間來,我們都很樂意為她跑腿、點燈。

低調、惜友、樂於為他人打燈
由於我也從事歷史寫作,十幾年前便有幸認識陳柔縉,就我認識的陳柔縉,非常低調,也很「惜友」。
十幾年前,社群平台還沒有現在這麼發達,朋友們知道我與陳柔縉相識,偶會託我向她邀請演講。對創作者來說,演講是極好拓展自己的知名度、帶動書籍銷量的機會,一般人應該都是來者不拒、多多益善的吧?但就我所知,那時候面對這樣的邀約,陳柔縉多數是婉拒的,她甚至會說她自己來婉拒對方,不讓我難做。我知道她低調,不喜應酬,願意與陌生的單位連繫,是為了不造成我在兩造之間傳話的麻煩,她的低調與愛護朋友,可見一斑。
我曾好奇地問,像她這樣有名的作家,明明可以享受許多讀者的簇擁,為什麼總是拒絕那些演講或採訪?她笑笑地說:「我不是學者啦,不會做什麼厲害的研究,不知道要跟別人講什麼,他們為什麼會想聽我講話……」說這話的時候,她的眼神是非常真摯的,絕不是那種「口嫌體正直」的以退為進。
她從不吝惜提攜後進,甚至她不認為那些是「後進」,而是一在文史領域開疆闢土的戰友,別人寫書恨不得沾一沾她的名氣,她也樂於幫忙其他人打燈,大方地為許多書掛名推薦,卻始終不願意站在鎂光燈前,成為焦點。
她也曾和我討論史料的出處,或是大方分享她找到的有趣資料或寫作靈感,她甚至豪氣地說過,有一批資料她蒐集到一半,遲遲未能寫,「就交給妳寫下去啦!」當然我最後並沒有承接了那些資料,但對寫作者來說,史料與靈感就是戰場上的兵馬,能夠把這些兵馬大方餽贈朋友,除了陳柔縉之外,我再也沒有遇過了。
庭園造景式的回憶錄書寫
知道老師因車禍而離開的消息,我心中先是一驚,想著這一定是假消息吧?這不是真的吧?一定是某個同名同姓的人,被張冠李戴的烏龍新聞吧?隨著消息越來越多,確認真的是陳柔縉老師離開了的那晚,我寐不成眠,時睡時醒,恍恍惚惚,腦中時不時浮現她一貫的笑容。
陳柔縉在羅福全回憶錄《榮町少年走天下》裡說,為他人代筆回憶錄「不是一件有聞必錄的抄工」,而是「比較近似庭園造景」,將他人記憶的庭園裡既有的材料加以修飾整理。有時候讀陳柔縉的作品,不得不佩服能將同樣的歷史材料造出這等美好的風景,是她才有的天賦,而上天將才氣縱橫又異常用功的陳柔縉賜給臺灣史寫作的領域,真的是送給這個領域最好的禮物。
我相信,酷愛說故事與寫作的陳柔縉,即使離開了,也一定又到了另一個世界的圖書館裡,在書架之間翻找歷史,準備好再說下一個精彩的故事了。
(本文為作者觀點,不代表本站立場)